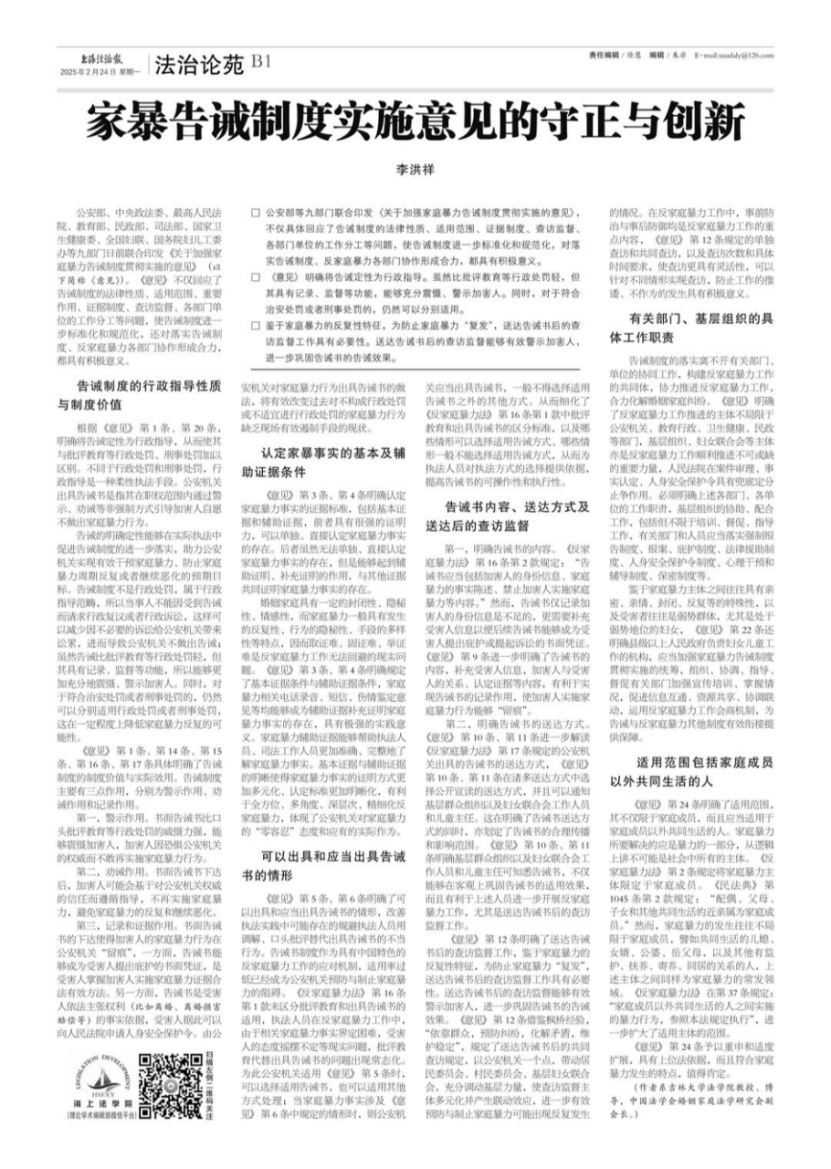李洪祥,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回应了告诫制度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重要作用、证据制度、查访监督、各部门单位的工作分工等问题,使告诫制度进一步标准化和规范化,还对落实告诫制度、反家庭暴力各部门协作形成合力,都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意见》第1条、第20条,明确将告诫定性为行政指导,从而使其与批评教育等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加以区别。不同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行政指导是一种柔性执法手段。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是指其在职权范围内通过警示、劝诫等非强制方式引导加害人自愿不做出家庭暴力行为。
告诫的明确定性能够在实际执法中促进告诫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助力公安机关实现有效干预家庭暴力、防止家庭暴力周期反复或者继续恶化的预期目标。告诫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属于行政指导范畴,所以当事人不能因受到告诫而请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这样可以减少因不必要的诉讼给公安机关带来讼累,进而导致公安机关不做出告诫;虽然告诫比批评教育等行政处罚轻,但其具有记录、监督等功能,所以能够更加充分地震慑、警示加害人。同时,对于符合治安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仍然可以分别适用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暴力反复的可能性。
《意见》第1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具体明确了告诫制度的制度价值与实际效用。告诫制度主要有三点作用,分别为警示作用、劝诫作用和记录作用。
第一,警示作用。书面告诫书比口头批评教育等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强,能够震慑加害人,加害人因恐惧公安机关的权威而不敢再实施家庭暴力行为。
第二,劝诫作用。书面告诫书下达后,加害人可能会基于对公安机关权威的信任而遵循指导,不再实施家庭暴力,避免家庭暴力的反复和继续恶化。
第三,记录和证据作用。书面告诫书的下达使得加害人的家庭暴力行为在公安机关“留痕”,一方面,告诫书能够成为受害人提出庇护的书面凭证,是受害人掌握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证据合法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告诫书是受害人依法主张权利(比如离婚、离婚损害赔偿等)的事实依据,受害人据此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由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行为出具告诫书的做法,将有效改变过去对不构成行政处罚或不适宜进行行政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缺乏现场有效遏制手段的现状。
《意见》第3条、第4条明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标准,包括基本证据和辅助证据,前者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可以单独、直接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无法单独、直接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但是能够起到辅助证明、补充证明的作用,与其他证据共同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
婚姻家庭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隐秘性、情感性,而家庭暴力一般具有发生的反复性、行为的隐秘性、手段的多样性等特点,因而取证难、固证难、举证难是反家庭暴力工作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意见》第3条、第4条明确规定了基本证据条件与辅助证据条件,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伤情鉴定意见等均能够成为辅助证据补充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家庭暴力辅助证据能够帮助执法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更加准确、完整地了解家庭暴力事实。基本证据与辅助证据的明晰使得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方式更加多元化、认定标准更加明晰化,有利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精细化反家庭暴力,体现了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态度和应有的实际作为。
《意见》第5条、第6条明确了可以出具和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改善执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规避执法人员用调解、口头批评替代出具告诫书的不当行为。告诫书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应对机制,适用率过低已经成为公安机关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阻碍。《反家庭暴力法》第16条第1款未区分批评教育和出具告诫书的适用,执法人员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由于相关家庭暴力事实界定困难,受害人的态度摇摆不定等现实问题,批评教育代替出具告诫书的问题出现常态化。为此公安机关适用《意见》第5条时,可以选择适用告诫书,也可以适用其他方式处理;当家庭暴力事实涉及《意见》第6条中规定的情形时,则公安机关应当出具告诫书,一般不得选择适用告诫书之外的其他方式。从而细化了《反家庭暴力法》第16条第1款中批评教育和出具告诫书的区分标准,以及哪些情形可以选择适用告诫方式、哪些情形一般不能选择适用告诫方式,从而为执法人员对执法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提高告诫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
第一,明确告诫书的内容。《反家庭暴力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然而,告诫书仅记录加害人的身份信息是不足的,更需要补充受害人信息以便后续告诫书能够成为受害人提出庇护或提起诉讼的书面凭证。《意见》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告诫书的内容,补充受害人信息,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关系、认定证据等内容,有利于实现告诫书的记录作用,使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能够“留痕”。
第二,明确告诫书的送达方式。《意见》第10条、第11条进一步解读《反家庭暴力法》第17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的送达方式,《意见》第10条、第11条在诸多送达方式中选择公开宣读的送达方式,并且可以通知基层群众组织以及妇女联合会工作人员和儿童主任。这在明确了告诫书送达方式的同时,亦划定了告诫书的合理传播和影响范围。《意见》第10条、第11条明确基层群众组织以及妇女联合会工作人员和儿童主任可知悉告诫书,不仅能够在客观上巩固告诫书的适用效果,而且有利于上述人员进一步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尤其是送达告诫书后的查访监督工作。
《意见》第12条明确了送达告诫书后的查访监督工作,鉴于家庭暴力的反复性特征,为防止家庭暴力“复发”,送达告诫书后的查访监督工作具有必要性。送达告诫书后的查访监督能够有效警示加害人,进一步巩固告诫书的告诫效果。《意见》第12条借鉴枫桥经验,“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规定了送达告诫书后的共同查访规定,以公安机关一个点,带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妇女联合会,充分调动基层力量,使查访监督主体多元化并产生联动效应,进一步有效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可能出现反复发生的情况。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事前防治与事后防御均是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点内容,《意见》第12条规定的单独查访和共同查访,以及查访次数和具体时间要求,使查访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针对不同情形实现查访,防止工作的推诿、不作为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告诫制度的落实离不开有关部门、单位的协同工作,构建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共同体,协力推进反家庭暴力工作,合力化解婚姻家庭纠纷。《意见》明确了反家庭暴力工作推进的主体不局限于公安机关、教育行政、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基层组织、妇女联合会等主体亦是反家庭暴力工作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事实认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兜底定分止争作用。必须明确上述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职责,基层组织的协助、配合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督促、指导工作,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报案、庇护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心理干预和辅导制度、保密制度等。
鉴于家庭暴力主体之间往往具有亲密、亲情、封闭、反复等的特殊性,以及受害者往往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意见》第22条还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应当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统筹,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培训、掌握情况,促进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运用反家庭暴力工作会商机制,为告诫与反家庭暴力其他制度有效衔接提供保障。
《意见》第24条明确了适用范围,其不仅限于家庭成员,而且应当适用于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家庭暴力所要解决的应是暴力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是社会中所有的主体。《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规定将家庭暴力主体限定于家庭成员。《民法典》第1045条第2款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然而,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不局限于家庭成员,譬如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的关系的人,上述主体之间同样为家庭暴力的常发领域。《反家庭暴力法》在第37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进一步扩大了适用主体的范围。
《意见》第24条予以重申和适度扩展,具有上位法依据,而且符合家庭暴力发生的特点,值得肯定。